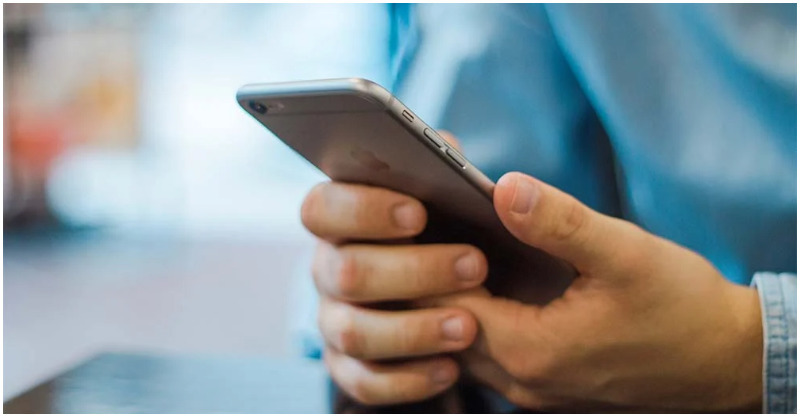亞索上單怎麼懟鱷魚和諾手?別打了,用頭鐵都打不過!
問下大家,快樂風男打上單咋安排下鱷魚和諾手(本文出處虎撲社區@默默契脾氣)
我是個非常喜歡玩風男的玩家,但是對線碰到這兩個,每次都要抗壓,經常頭都要被他們兩個錘的不要不要的…這兩個英雄真的不太和你講道理,鱷魚就是眩暈你打你一套在轉走……諾手就不要說了,只要我一個失誤,他疾跑一開我就涼了……死一次我就基本沒有對線了,經常被他吊打到遊戲結束。

@神牛跳大閃折腰:你要相信,亞索這個英雄只要技術好,操作起來是可以一打五碾壓一切的
@白狂龍:這玩意本身就是用來欺負一大堆法師中單的,你為啥非要頭鐵去打上路肉搏?中路不能混了么?更何況玩打野最喜歡抓的就是亞索,你還去玩上路。
@abb須:風男上班對線安排了我鱷魚,我60勝率,不過打團我安排了他

@安菲爾德8號球童:我只希望rank遇到你你在對面。
@底線滑翔劈扣不中:亞索現在在中路都不能想e就e。前期刷就完事了,傳送留著。起飛了就帶到死。
@Illlllllll :英雄屬性本來就打不過,1級可以欺負下這2個,2級可能就有點打不過了,3級開始抗壓。如果打野針對下,很容易炸,鱷魚諾手到6了配合個傷害高點的打野隨便越。
@一統漿糊:風男打不過諾手,打鱷魚不要e一集學q上去猛q壓了血量前期就好打了,之後能不能打過就要看你的水平了
@默默契脾氣:我只玩風男和捅男。也不能算很坑吧。就是安排不了這兩個兄貴。太剛了

@禮拜六杜少時刻:諾手鱷魚玩家觀點:主系對自己操作有信心點征服者 要求穩就迅捷步法副系盡量點堅決系因為亞索的硬度和這倆哥們比差太多 綠叉出來之前如果發現對面水平不低就穩著打 因為鱷魚諾手對線強度都很高 亞索被殺一次基本就失去了前中期一對一對拼的資本

特別是那種對面特穩的裸布甲鞋的真不能有任何失誤 總之亞索打上單不能玩太騷要耐得住性子 可以控線等隊友gank來度過前期 等有一定等級和裝備支撐才能和一眾戰士扳扳手腕 而且上路亞索比中路更容易針對更加要求穩 反正那些前期瘋狂e上來消耗我的亞索基本最後都被通關 我自己偶爾玩亞索都不敢走上路因為容錯率太低操作有瑕疵基本很難打贏常規戰士上單
小夥伴,你們怎麼看?
銳雯跟著亞索去種田了?LOL官方更新兩人的故事:破刃的懺悔

英雄聯盟宇宙官方故事:第一章——破刃的懺悔
耕犁的尖端深深地掘進表土,將整個冬天埋藏其下的部份翻出,向初春的天空打招呼。銳雯走過牛車後面的小田,將注意力集中在握穩掌上寬大的把手,以及從自己嘴中笨拙說出的異邦詞語。
「耶麥。非亞。斯伐撒。阿拿。」
每走一步,都能嗅到空氣中瀰漫著新生大地蘇醒的土壤氣息。銳雯一邊走著,一邊緊緊握住木頭。在過去幾天里,這柄粗糙的把手又喚醒了放置已久的老繭與轉瞬即逝的記憶。
銳雯咬著嘴唇,停止胡思亂想,繼續著手正事。「母親。父親。姊妹。兄弟。」
骨瘦如柴的牛轉了轉耳朵,拉動耕犁揚起的細小碎石彈到了銳雯身上,但她完全不在意。她穿著粗織的襯衫,沾滿污垢的袖子卷了起來;相同質料的長褲則早已染成土黃色。這套穿著的袖口對其原本的主人會顯得太短,但穿在銳雯身上,足足能夠蓋住她裸露的腳踝和底下那雙簡陋的泥鞋。
「耶麥。非亞。斯伐撒。阿拿。」銳雯繼續背誦,嘗試記起這些字詞。「而哉,兒子。蝶達……」
她沒有放慢腳步,用袖口抹去從濡濕頭髮滴至眉上的汗水。她的手臂肌肉發達,能夠很輕鬆地就用單手握住耕犁。農夫已經進到屋裡去用午餐與補充水份。老人告訴銳雯可以先稍事歇息,等到森林的陰影覆蓋再繼續上工,但她堅持要完成。
一陣清新的微風撫過銳雯汗濕的後頸,她抬起頭來環顧四周。諾克薩斯帝國曾想逼迫愛歐尼亞屈服於他們的意志。面對愛歐尼亞的頑強抵抗,諾克薩斯採取了強硬的手段。銳雯在耕犁後繼續她的沉思步調。即便諾克薩斯帝國的力量遍布,春天的腳步照樣會到來。距諾克薩斯被趕出已一年有餘,被污染的雨水與泥土最終還是孕育出了嫩綠的芽。萬物的姿態看起來就彷佛一切都有了新的開始。希望真的是這樣。銳雯嘆了口氣,分岔的發尾輕劃過她的下巴。
「蝶達,女兒。」她又果斷地回到了背誦,雙手握著木製手把。「耶麥。非亞。」
「那其實是念做發-也,」一個從森林中傳出的聲音說道。
銳雯的動作突然中斷,乾瘦的牛也頓時被皮韁繩牽制,耕犁猛地掘進一塊泥土,因挖到石塊而發出金屬的聲響。
說話的聲音不是老人的。
銳雯緩慢地從唇中吐息,藉此放鬆呼吸。雖然傳來的聲音只有一個,但也藏有更多人的可能性。多年來的戰鬥訓練告訴她要進入防禦狀態,但她只是維持不動,盯著眼前的耕犁與牲畜。她覺得太輕了。此刻她緊緊握著耕犁的木柄。在她的身旁應該要有個更重的存在感,但她只有一把輕得幾乎讓人無感、置於右臀的小短刀。拿來削削一些蔬果倒是挺好用,不過除此之外也就沒其它功能了。
「那個詞念做發-也,」
出聲者終於在有一整片琥珀松樹的農田邊緣現出身影。
「兩個字中間有停頓,」男人說著並邁步向前。他的後腦扎著一大束蓬密的黑髮,肩膀附近戴有一件編織披風。銳雯察覺到披風沒有完全覆蓋他左肩的金屬鎧甲,也沒有遮掩他身側的無鞘刀劍。他也曾屬於武士階級,但並不屬於任何麾下。他就是一個流浪者。
她當下就判斷這男人是危險的。
「發-也,」他又示範了一次發音。
銳雯沒有回話。並非因為不知道該說什麼,而是顧慮到自己的口音。她繞著耕犁移動,將其放置在自己與發音標準的男人之間。她塞了一縷髮絲在耳後,彎下腰來檢查耕犁的狀態,裝作很關心剛剛卡到的石塊。雖然用途是切割草皮與粘土,但耕犁的刀刃比起她的小短刀要有用多了。她在某個早晨看過老人如何將其固定在木身上,所以她知道要怎麼拆開。
「我最後在這裡時沒印象有看過你,不過我也離開很久了,」男人說道。他的聲線透露一種流浪許久才會有的淡定與粗野。
銳雯還是拒絕打破兩人之間的沉默,使得昆蟲的嗡鳴聽起來越發響亮。
「我聽說由於索瑪長老逝世,執法官都被喚來提出新的證據,」男人又繼續說著。
銳雯無視他,拍了拍生病的牛。她像熟悉馬匹等農場動物的人一般,手指沿著皮帶撫摸,趕走漆黑牛眼旁飛舞的小蟲。
「如果你是新來的,或許對那樁謀殺知之甚少吧。」
這番話讓她抬頭與陌生男子的眼神相交,無辜的牲畜就杵在他們中間。銳雯看見一道疤痕跨越了男子的鼻樑,不禁想知道干出這事的人是否還健在。男子的眼神泛著冷酷,但又有好奇隱藏其下。銳雯感到土地的震顫透過了泥鞋的薄底。天空萬里無雲,卻傳出一陣如雷的悶響。
「有人來了,」男子說道,臉上帶著微笑。
銳雯往老人農舍所在的小丘眺望,看見六名武裝騎士出現在山脊,與他們的坐騎朝往一片耙過的小田。
「她在這,」其中一人說道。他的口音很重,銳雯費勁分析她努力學習的語言的細微差別。
「不過……她一個人嗎?」另個人問道,在樹蔭中瞇起眼睛。
一道清風迅速地纏繞在耕犁與銳雯周圍,接著便溜回森林的陰影里。銳雯看向陌生男子原本的所在處,但他已消失無蹤,然而前來的騎隊讓她沒時間去思考了。
「可能是鬼喔,」領隊說道,對著他的人嘲笑。「被她殺掉的人跑回來複仇啰~」
騎士們策馬快跑了起來,團團圍住銳雯,踩壞她那天清晨挖好的溝渠。領隊的坐騎背上載著一束裹著布的堅硬物體。銳雯的眼神跟著她身邊的馬匹移動,鬆散的土地在馬蹄踐踏下又變回冷硬的粘土。
她最後瞥了一眼犁刀。有兩名騎士備有弩。在她能解決掉一個之前,自己就會先被擊倒了。她的手指發癢,想觸碰那把潛在的武器,心中卻祈求他們能夠靜止。
緊張感很快地使她繃緊了肌肉。身為長期受過戰鬥訓練的人,不會簡簡單單就為了求和平而舉白旗投降的。她的耳里湧進血液奔騰的聲響。你會死的,那個震耳欲聾的聲音咆嘯著。但同時,他們也一樣會。
銳雯的手指開始往犁刀移動。
「放了她!」因為要能夠把四處遊盪的奶牛給叫回來,這名農妻的嗓門可大得很,而剛剛在田野間響起的吼聲打斷了銳雯想同歸於盡的衝動。「亞薩,快點!你得想想辦法!」
當農夫與他的妻子抵達山丘時,圍著銳雯的騎隊們也都停止了動作。銳雯用力地咬了臉頰內側一口,襲來的劇痛讓她集中精神,平息了戰鬥的慾望。她不能讓愛歐尼亞人民在他們的家鄉濺血。
「我說過我們辦好事之前,要你們待在家裡的吧?」領隊對他們說道。
名為亞薩的老人蹣跚地走過崎嶇不平的泥土。「她沒做錯事。我才是帶那個來的人,」他指著裹布的堅硬物體說道。「我會回答的。」
「康提先生。歐法,」領隊說道,嘴角扯出一抹擺出恩賜態度的微笑。「你知道她是什麼。她已經犯下了很多罪。要是給我做主,我就會在她現在站著的地方砍了她,」他俯視著銳雯,然後煩躁地皺起鼻子。「老頭,很不幸地,你想說的話得留到審訊了。」
在領隊說完后,銳雯的腳便陷進潮濕的泥土中,瞬間就被箝制住。插翅難飛的困境壓倒性地襲來,令她難以承受。她掙扎著想重回自由,加快的脈搏變成淺薄的節拍,冷汗於雙肩之間不斷滲出。她的心思跌進了不同的時空,那裡的馬匹噴鼻嘶鳴,蹄鐵踐踏過染血的大地。
在更多不願想起的記憶湧現之前,銳雯緊緊閉上眼睛,接著深吸了一口氣。她告訴自己:滋潤這片土地的是春雨,而非死者的鮮血。當我睜開雙眼,只會看見生命蓬勃的光景。
她睜眼時,田野還是那片才剛剛翻鬆過的土地,而非一片空曠的墳場。騎士的領隊翻身下馬,手持一對鐐銬朝她走近。比起任何要在她家鄉拘禁罪犯的東西,愛歐尼亞的旋金要美麗得太多。
「你沒辦法擺脫過去的,諾克薩斯的走狗。」領隊耀武揚威地說道。
銳雯的目光透過犁刀往上移至老夫婦。他們面容上的歲月痕迹已經負擔太多痛苦,而她不能再增添上去了。她絕對不能。銳雯試著盯住眼前的情景:老夫婦兩人相互依偎,緊緊地擁著彼此。那是知道即將失去什麼的時候,所做出雖脆弱卻孤注一擲的反抗。當老農夫以袖口擦拭淚濕的臉龐時,銳雯終於不忍卒睹而別過頭去。
銳雯將手腕伸向騎隊領導。她冷冷地瞪視他沾沾自喜的笑容,讓那副鋼鐵銬住了自己。
「別擔心,蝶達,」農夫妻子大聲地說出。銳雯可以聽出那聲呼喊當中帶著繃緊的希望。那份希望太沉重了。銳雯被帶往越來越遠的地方,焦慮的詞語隨著微風消散,方才的氣味也轉變為泥土的氣息。「蝶達,」它輕聲耳語著。「我們會讓他們知道你的身份。」
「蝶達,」銳雯也喃喃地回應。「是女兒。」

女孩投降后兩天,夏瓦.康提只是幫丈夫緩慢地修復被踏壞的犁溝,並替農田播種。這些工作有女孩幫手時輕鬆許多,不過若他們的兒子還在世的話也會是如此。只有她和亞薩兩人是沒辦法做完全部的。
審訊當天的清晨頗為寒冷,兩夫婦自知他們年邁的身軀需要花費不少時間才能走過通往城鎮的漫長道路,於是在日出前便動身前往村莊的議事廳。
「他們知道她是諾克薩斯人。」
「你擔心得太多了,」夏瓦說道,用舌頭髮出咯咯的聲音。想起自己的聲調比丈夫還擅長安撫雞隻,她對他抱以一個充滿希望的微笑。
「她是諾克薩斯人。光這件事就足以讓他們宣判有罪了。」亞薩的半張臉埋在脖子周圍的手織羊毛圍巾里,碎念著他的想法。
夏瓦的人生有大半輩子都在哄騙固執的牲畜們走向屠夫的刀下。她暫停了一下,將臉轉向丈夫。
「他們並不像我們這麼了解她,」她戳著他的胸膛說道,透過手指宣洩她的惱怒。「這就是為何你必須替她說話的原因,你這頭老笨羊。」
亞薩很了解他的妻子,明白再繼續爭辯下去也不會改變她的心意。夏瓦不滿地悶哼一聲后回到路上,兩人便安靜地前往城鎮中心。人潮開始湧進議事廳,她見狀便加快腳步,為了找到更靠前的座位而擠進長椅間的狹窄空間……然後唐突地被一名睡眠中男人的腿給絆倒了。
當這名老婦人發出虛弱的呼聲往前傾倒時,睡眠中的男人也傳出呻吟。他的手迅雷不及掩耳地伸出,在老婦人摔進石頭地板前以臂膀穩穩地接住了她。
「你應該注意腳步的,歐瑪,」陌生男子謙恭地低聲說道。他的呼吸很沉重,但說起話來不帶一絲含糊。老婦人站穩后,他的手也隨之收回。
老婦人雙眼瞇起,盯著這位神奇的救星。察覺到她密集的目光后,男人的臉默默縮進肩膀戴著的披風裡,鼻樑上那道突兀的疤痕便覆蓋在陰影中。
「即使是在深夜乾的惡行,也逃不過議事廳的,年輕人。」夏瓦整理了一下長袍,稍微揚起的下巴明顯透露輕蔑。「一位女人接下來的人生將在今天決定。我勸你在被執法官要求承認你的錯誤之前,先行離開這裡吧。」
「夏瓦,」老人趕了上來,一隻手放在妻子的臂上。「今天要是想幫上忙,你可得控制住脾氣啊。他沒有要造成傷害的意思,離開他吧。」
蒙面的男人以平靜的祈求舉起兩隻手指,依舊掩著臉孔。「你真是說到重點了呢,歐瑪,」他用幽默的語調說道。
夏瓦繼續移動,小心翼翼地按捺著怒氣。老人經過時稍微點了頭致意。
「別太快就評斷她,年輕人。她只是擔心真相大白前,會有無辜的靈魂被烙上罪惡的印記。」
在老人繼續移動時,蒙面男認同地咕噥:「我們的想法在那一點上是一致的,歐法。」
老人因那句奇怪的私語而回頭瞥了一眼。座位空無一人,只有一陣微風吹過附近一對正在交談的夫婦,他們飄動的長袍沙沙作響。蒙面男子早已撤進議事廳遠方的陰影中。

夏瓦在前方聚集的群眾中選了一個座位。木凳上的平滑紋路應該是令人感到舒適的 - 它們是由木織者為了盡居民義務提昇平衡與和諧而塑形 - 但老婦人卻找不到一個自在的位置。她瞥向丈夫,他已經耐心地坐在一張嘎吱作響的凳子上,等著被傳喚。亞薩身邊站起一名法警,在用木簽剔牙。老婦人發現那名法警是梅歐克,也就是之前來逮捕銳雯的騎隊領導。她怒瞪著梅歐克,但他完全沒有注意到。他正看著房間後方的大門。當三名穿著黑袍的人物從開啟的門中步出時,他便迅速地挺直身軀,並吐掉嘴裡的木簽。
執法官坐上頭桌的位子看著擁擠的大廳,法衣有條不紊地鋪在身後。嘈雜的大廳頓時就變得鴉雀無聲。三個執法官當中,一名有著鷹勾鼻的高瘦女人肅穆地站立著。
「本次審訊將提出有關索瑪長老逝世的新證據。」
一陣如數百隻蝗蟲齊鳴的低語開始從人群中央某處散開。有些人已經聽說了執法官所謂的新證據,但大部份的人只因「他們之中有諾克薩斯人」的謠言而聚集於此。不過謠言改變不了眾所皆知的既定事實:索瑪長老的死並非秘密。操縱風的技術與冥想堂留下的魔法都是必要的證據。除了索瑪,只有一人能夠達到如此境界。
尚未痊癒的傷口綻裂,群眾蜂擁的思緒凝聚在一個共有的苦痛之中。若長老沒有倒下,他們互相高喊,村莊就不會遭受如此龐大的傷亡。謀殺發生后沒多久,有半數諾克薩斯軍隊在往那歐途中屠殺了許多人,無數兒女因此痛失雙親。在索瑪長老之死所帶來的悲痛失衡中,諾克薩斯的入侵攻勢越發壯大。更糟糕的是,村民只將責任全歸咎在一個自己人的身上。
在一片混亂中,一道清晰的嗓音劃出。
「我們都已經知道是誰殺了索瑪長老,」夏瓦蠕動著飽經風霜的雙唇說道。「就是那個叫做亞索的叛徒。」
眾人頷首,不容質疑的尖銳同意在暴民當中如漣漪般蕩漾開來。
「有誰會索瑪操縱風的技術?就是亞索!」夏瓦補充道。「永恩出走追捕他無可饒恕的弟弟,如今都還未歸來。那個懦夫也該對此負起責任。」
群眾再次咬牙切齒了起來,這次還大聲疾呼要亞索血債血還。夏瓦更放鬆地安頓在長凳上,對於罪魁禍首重新指向正確人選的局面感到滿意。
鷹勾鼻執法官來自一個悠久的木織者家族,其因能夠解開與舒展樹瘤而聞名。她舉起一個堅硬栗子形成的完美圓球體,接著果斷地敲擊其烏黑的支架。刺耳的聲響令群眾陷入沉默,大廳再次回歸秩序。
「本法庭欲尋求的是關於索瑪長老逝世真相的見聞與啟發,」執法官說道。「你希望的是阻礙啟發嗎,夫人……?」
老婦人看著她的丈夫,感到臉頰發熱。「康提。夏瓦.康提,」她以與大膽沾不上邊的語氣回應,低下了頭。凳子上的老人看著她,抹去自己禿頂上閃亮的汗珠。
「如我所說,我們在此是為了接受新的證據。」鷹勾鼻執法官望進人群,審視是否還有頑固的異議者存在,接著便向梅歐克法警點頭,「請帶她進來。」
- 下回待續 -
除此之外,還有兩張漫畫預告,台服翻譯大家先湊合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