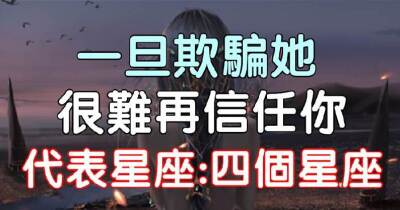為了活下去,我被迫認了七位師傅,然而這七位師傅卻是一個人……

我叫周曦,我在一個不見天日的地方,伴著幽明的人皮燈籠,如死人般渾渾噩噩的度過了五年,事情要從五年前說起。
2010年8月24日,說來也巧,那天是農曆七月十五,也就是鬼節,全年陰氣最重的一天。
下午四點多,我還在醫院上班,手機突然響了,「閨女,家裡出事了,你趕緊回來一趟……」我爸顫抖的聲音從電話里傳來,似乎在儘力的壓制著某種恐懼,我心裡不禁咯噔一下,立馬要問什麼事,電話瞬間掉線了,我趕緊撥回去,我爸手機卻關機了,我頓時一驚,心裡隱隱的覺得有些不安。
我當時正在鎮里一家醫院外科實習,接到電話后就立刻請假,搭上長途車便回家了,鎮里到我老家只要2個小時的車程。
我老家住在東北一個叫老龍頭的小山村,我們整個村子的地勢東高西低,離遠看就像一個盤著身子的巨龍,村子正好在盤龍的腹部,龍頭一直延伸到離村口不遠的密林里,村裡的老人們都說這種盤龍的風水會招來神靈保護我們,只不過很少有外地人敢來我們這,甚至談此色變,因為整個村子都從事撈口口的行業,所謂撈口口,其實就是賺死人的錢。
我從小沒媽,家裡還有個小我六歲的弟弟,我爸是個二皮匠,主要工作是縫合屍體,跟現在的殯葬美容師差不多,中國人講究死有全屍,來找我爸縫合屍體的一般都是橫死的,死狀比較慘。外人看來這份工作很滲人,我爸卻不以為然,總說能用這份手藝,為他們的人生最後潤色,也未嘗不是積德行善的方式,見識多了這些,自然也就不害怕了。
一路上我給我爸打了無數遍電話,依舊是關機,我心裡有些慌了,車到站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立刻往家裡飛奔,剛準備敲門,發現門微微的開了一條小縫,我立刻心生警惕,試探著問,「爸?老弟?」沒有任何人回答。
我試探著打開門一看,屋子裡一片狼藉,就像剛剛被人洗劫了一樣,地上布滿了黑鞋印,這腳印奇大,我一眼就認出來絕對不是我爸的,似乎有人是要找什麼,腳印旁邊還有幾滴橙黃色的東西,我上前看了一眼,頓時倒吸一口冷氣,這是屍蠟!
突然,內室里傳出窸窸窣窣的聲音,好像有人在裡面說話,而那間內室正是我爸縫合屍體專用的,平時從來不讓我們進入,我起了一身白毛汗,當時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往門外跑,跑的太急,我直接撞在了一個人身上,我大聲尖叫,那人卻突然說話了,「小曦,你這是怎麼了?」

這聲音似乎有點熟悉,我鎮定了一下情緒,定眼看去,原來是我二叔,他正用充滿紅血絲的眼睛看著我,「我爸說家裡出事了,也沒說什麼事,手機還關機,我回來的時候門就這麼開著……」我邊解釋邊往內室的門瞄了一眼。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二叔的表情很詭異,某一刻我甚至感覺他的半邊臉似乎在笑,「我找你正是這事,應該是你爸走的太急忘了鎖了,咱們來客人了。」我當時沒反應過來,等明白后不禁十分訝異,我二叔所謂的來客人其實是行話,意思就是有屍體需要縫合,做為外科實習生,從小又看慣了這些,對我來說自然不是難事,我狐疑的是,這事怎麼找上我了,我爸一直很反感我接觸這些。
二叔好像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釋道:「山上的考古隊出事了,村裡的人都趕著去救人了,有兩個客人剛找到,你爸讓你幫忙整理一下。」說完,二叔嘆了一口氣,手裡抬著裹屍袋往內室走,我突然想起來我剛剛聽見內室有聲音,剛要提醒我二叔,結果他已經進去了,我趕緊跟在他身後,探頭往內室看了一眼,裡面很小几乎一目了然,除了操作台和一些工具外什麼都沒有,難道剛剛的聲音是我聽錯了?
我打開內室里昏黃的燈,二叔拉開裹屍袋將兩個「客人」放在操作台上,我找出工具箱,扯上專用的針線準備開始縫合,我掃了一眼兩具屍體,頓時倒吸了一口冷氣,他們的頭和脖子幾乎已經分離,最詭異的是脖子傷口處參差不齊並且嚴重變形,那感覺就好像是頭被人硬生生的從脖子上拽了下來,兩個死者都瞪大了眼睛,臉上的表情劇烈的扭曲。
「這……」我驚的幾乎說不出一句話來,雖然見慣了屍體,也著實被這死相嚇了一跳,我鎮定了一下情緒便開始整理和縫合,心裡卻止不住的疑問,他們到底在山上發生了什麼?
前陣子我們村裡來了一隊人,自稱是考古人員,說我們這裡是遼金的古戰場,可能存在大型的古墓群,我二叔一聽頓時來了精神,一直給他們充當嚮導,最後的挖掘地點定在了山上的密林里,我爸聽說了就強烈反對,那地方正好是龍頭所在之地,我爸當時說龍頭一旦被挖,村子里的天然擋煞屏障就消失了,盤龍有尾無頭,是大凶之兆,若是再有古墓群,整個村子都會變成聚陰之地,我二叔當然嗤之以鼻,說我爸太過迷信,都什麼年代了還相信風水,因為這事他們倆吵過好幾次。
「二叔,山上墓怎麼回事,這兩人……」屋子裡靜的可怕,我只能聽到自己的呼吸聲,我突然說了一句話嚇了二叔一跳,他一直在盯著我縫合那個客人,不知道再想什麼。
二叔面色凝重,他全身不自覺抖了一下,似乎很不想回答這個問題,緩了片刻,道:「山上那墓有問題,考古隊挖了很久,黑土下面覆蓋的居然是黃沙,這兩個人剛站在黃沙上面就……就陷進去了……」
「陷進去了?」我加重了語氣,心裡尋思沙子又不是沼澤地,怎麼會把人陷進去,他們到底在黃沙下面遇到了什麼,會如此死狀,兩個人都是斷裂在了脖子處,我不禁有些擔心我爸和弟弟,剛想繼續追問,我二叔的臉突然陰鬱起來,一如剛進門之時,似笑非笑,襯著屋裡昏黃的燈光,讓人覺得后脊背發涼。
「快點吧,我還有事呢——」二叔不耐煩的催促起來,拖著長聲,跟剛才判若兩人。
我倒吸了一口冷氣,手上的針有點顫抖,縫合的時候,我又發現一個詭異的細節,他們兩人心臟之處都紋著相同的紋身,乍一看紋身類似錶盤,只是錶盤之內似乎還寫著某種符號,而我並不認識。

見我縫合完畢,二叔將他們重新包裹在裹屍袋內,朝著我裂嘴一笑,「再見——」二叔那語氣好像跟我永別一樣,我當時只覺得他莫名其妙。
二叔走後,我將內室收拾了一下準備出來,一眼撇到了牆上供奉的神龕,這內室我爸從來不讓我們姐弟倆踏入,那神龕用黃色的布罩著,我很好奇神龕裡面是什
么,我躡手躡腳的走過去,掀開黃布,裡面的東西有點出乎我預料,只是一個紫檀色神像,看上去好像是一個女人,雕刻的很仔細,她閉著眼睛,手裡拿著好像錐子的東西,她的穿著很奇怪,有點像古代的長裙,我還在納悶這個神像是誰。
折騰了半天,已經晚上十點多了,我爸仍不見回來,我越想越覺得今天的事詭異,尤其是那兩個人的死狀,尋思著眼皮便開始打架,渾渾噩噩的我聽見內室里有人說話。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發現屋裡漆黑一片,內室的燈居然亮了,我倒吸一口冷氣,探著身子往裡看,突然一張滿是鮮血的臉朝我看來,我嚇的趕緊往後退,我能感受到陣陣陰風從內室里刮來,裡面有一個人,他使勁的用手拽自己的頭,惡毒的看著我,而那個人正是我剛剛縫合的客人,然而我縫合的線卻結結實實的纏繞在他的皮肉之間,他拚命的想掙脫開,臉上露出極其痛苦的表情。
我一驚,立馬恢復的意識,轉身準備往外跑,而另一個「客人」卻站在我的身後,他們兩個離我越來越近……與此同時,我聽到內室的神龕里發出「嘶嘶」的聲音,如同蛇吐信子一般………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感覺到周圍劇烈的顫動,好像有人在使勁的推我,耳畔傳來熟悉的聲音,「小曦……小曦……」那聲音由模糊到清晰,我漸漸的睜開了眼睛,映入眼帘是我爸熟悉的臉,此刻我躺在了內室的地上,而那兩個「客人」卻已經不見了蹤影,剛才是幻覺嗎?可為什麼那麼真實,我正在心裡捉摸著。
「你怎麼回來了?怎麼還會暈在這?」我爸焦急的問道,他紅腫的眼睛已經布滿了血絲,身上好像還受了傷。
我眨巴眨巴眼睛說「不是你讓我回來的嗎?我給你打了一天電話都關機,我弟呢?二叔說你們都上山救援去了,他還抬了兩個屍體讓我縫,到底發生了什麼?」我一臉的迷惑,總覺得今天的事特別詭異。
我爸聽到我提到二叔,立馬倒吸了一口冷氣,表情扭曲起來,「你……你看到你二叔了?」他用難以置信的口吻問道。
我恩了一聲,把之前的事情講了一遍,我爸全身抖了起來,額頭上出現大滴大滴的汗珠,「你說那兩個客人的心臟處有類似於錶盤的紋身?」我爸突然打斷了我,問道。
我茫然的點點頭,突然他仰天大笑一聲,惡狠狠的說了一句,「到底還是讓他們算計了。」說完,我爸看了一眼牆上的表,當時正好是半夜11點40分,我爸沒在說話,從內室柜子里拿出幾個竹籤子擺弄起來,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當時一頭霧水,繼續追問,「讓誰算計了?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爸沒有回答,他將幾根竹籤子圍城了一個簡易的燈籠形狀,便開始往那燈籠上糊紙,那紙白的刺眼,仔細看又似乎不是紙,他眼睛一直瞄著牆上的表,屋裡靜的嚇人,過了大概十分鐘,燈籠完全做好了,他往裡放了一隻白色的蠟燭,將燈籠遞給我,說:「拿好它,趕緊走,別讓燭光滅了,走的時候不管誰在背後喊你,都不要回頭。」
我當時一愣,見我爸一臉認真的表情又不像開玩笑的,「可是我上哪去啊?」我皺著眉頭問道。
我爸摸摸我的頭,用不舍的眼神看著我,道:「小曦,我根本沒給你打過電話,我一直在山上參加救援,要救的人就是你二叔……」我爸倒吸了一口冷氣,「那兩具屍體胸口上類似錶盤的紋身,是邪術之中的用來制惡鬼的符咒,他們在死之前含了極大的怨氣,你一定是縫錯了他們的頭,這兩個惡鬼如今已經纏上你了,這一切都是別人的算計好了……」
我才想起來,縫合屍體的時候,兩個屍體都是我二叔擺好我直接縫合的,如果我爸上山是為了救二叔,那我見到的二叔又是誰?聯想起剛剛二叔那似笑非笑的臉,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我剛要繼續問下去,突然傳來一陣急促敲門聲,聲音很大,好像要把門敲碎一般,我爸撇了一眼牆上的表正好是十二點,他趕緊點亮那燈籠,遞到我手上,沖著我大喊一聲,「沒時間解釋了,快走……」
我不知所措的接過燈籠,根本不知道該去哪,一抬頭髮現在燈籠的照射下,內室牆面上出現了一個小門,裡面黑漆漆的什麼都看不到,隱隱的卻能感受到陣陣陰風,之前進來的時候牆面上還什麼都沒有,這門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現在想不了那麼多,我爸使勁往那門裡推了我一把,等我再回頭,身後已經是一片漆黑,我不知道自己置身在什麼地方,只能提著燈籠,跌跌撞撞的往前走。
我周圍似乎瀰漫著一片黑霧,蠟燭微弱的光根本照不透這些黑霧,我的意識漸漸的開始模糊不清,渾渾噩噩的只知道一直往前走,突然,我聽到似乎有人在背後喊我的名字,隱隱的覺得有一雙手拍在我肩膀上,當時腦子裡一片空白,剛要回頭,霎時想起了我爸的告誡,無論聽到看到什麼都不能回頭,我嚇的一激靈,冒了一身冷汗,這才清醒過來,這蠟燭燃燒的很慢,只能照亮我到腳下的路,我低頭的時候,隱隱約約看到地面上好像有人臉,我趕緊收回目光,繼續往前走。

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旁邊出現了一個茅草屋,門緊閉著,我鼓足勇氣上前敲了敲門,從屋裡傳來緩慢的腳步聲,我頓時屏住呼吸,門緩緩的開了,一個滿臉皺紋的老人站在門口,她穿著一襲黑衣,頭上戴著一個奇怪的帽子,她緊閉雙眼,卻似乎上下不停的打量著我,「人皮燈籠……似乎很多年沒見了……」老人用低沉的聲音自言自語了一句,我剛要說話,她把門大敞開,「進來吧……」說完她轉身往屋裡走去。
我猶豫了片刻,跟她進了屋,一股刺鼻的腥臭味傳來,熏的我一陣反胃,老人一句話不說,坐在桌子旁不停的在一張白布上穿針引線,她一直閉著眼睛,屋子裡漆黑一片,她卻縫的遊刃有餘。
我不敢多言,提著燈籠在屋子裡看了一圈,牆上掛了很多銹品,大小不一,但都是用白布為底,上面的圖案都是一張一張的人臉,繡的栩栩如生,只是離遠看每張臉都是慘白色,煞是詭異。
我頓時覺得這白布有點眼熟,我隨手上去摸了摸好像是某種皮,跟我這燈籠上糊的是一種材料,我頓時想起那老人剛才的話,人皮燈籠,難道這牆上的都是人皮?我立馬覺得一陣噁心,身上起了一層白毛汗,我看向那老人,不禁倒吸一口冷氣,剛才沒注意看,她的眼睛居然是用線縫在了一起,等回過神來,我趕緊往門口走,那老人突然開口了,「你要幹什麼去,在這裡你不可以亂走,出了這屋子你就沒命了,除非你也想被掛在牆上。」
我頓時心裡一驚,「這……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你……你是誰?」
老人哼了一聲,「你就在這裡住下,記住,不要亂跑。」
我沒聽老人的話,剛準備提著燈籠往外跑,突然門自己開了,老人迅速轉向我,大聲說:「把燈籠舉過頭頂。」我當時懵了,不過還是照做了,我詫異的盯著門的方向,一個全身血淋淋的人走了進來,他故意低著頭,我看不清他的臉。
「你在跟誰說話?」那人用沙啞的聲音問道,並且四處的看,他的目光掃過我的時候,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他的臉血肉模糊並且已經腐爛,根本分辨不出五官,身上沾滿了黃沙,奇怪的是,他似乎看不到我。
老人鎮定自若,「自己跟自己說話,逗個趣兒而已。」
那人點點頭,「我的臉綉好了嗎?」
老人恩了一聲,指著牆角一張人皮說:「在那裡,自己去看吧。」老人仍然繼續手中的活沒有停下來。
那人順著老人指的方向,湊過去看了看,摘下牆上的人皮,小心翼翼的貼在自己的臉上,朝著牆上的鏡子照了照,不禁誇讚道:「跟我之前簡直一模一樣。」
他轉向我的時候,我用左手死死的捂著自己的嘴,生怕我大吼出來,這個人,這張臉,我都再熟悉不過,不是別人,正是我二叔,此刻的他面無表情,臉上沒有一絲血色,眼睛無神,就如同兩個空洞一般。

我剛要張嘴說話,老人似乎看穿了我的動向,朝我使了一個陰鬱的表情,我二叔留下了一塊玉似的東西,歪歪扭扭的便出了門消失在黑暗中。
「剛才那人是我二叔,他到底怎麼了?」我急忙問道。
老人歪著嘴笑了一聲,「能來這裡的,都不會再是活人了……」
我全身打了一個寒顫,沒敢再繼續問,老人拿起那塊玉,不停用手上針刻畫著什麼。
就這樣,我不知道在這茅屋裡呆了多久,一有人來買人皮,我就用人皮燈籠照著自己,他們無一例外都沒發現過我的存在,我每天吃的都是些乾癟的果子,老人很少跟我說話,而從那天起,我再沒見過二叔。
燈籠里的蠟燭燃燒的很慢,但一點一點再減小,突然有一天,老人對我說:「蠟燭要盡了,你可以走了,把這個帶上。」她扔給我一塊玉佩,正是二叔當時仍在這換人皮的,她似乎又在玉佩上刻了一些文字。
時仍在這換人皮的,她似乎又在玉佩上刻了一些文字。
我恩了一聲,心裡很想念我爸跟我弟,我的危險終於過去了,估計那兩個惡鬼不會再找我了。
老人將門打開,大笑了一聲,看穿我心思一般,說:「一切才剛剛開始。」說完這話,整個茅屋都離我越來越遠,我覺得周圍天旋地轉,便暈了過去。